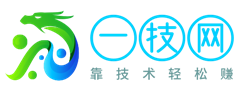有上海朋友看了王家衛(wèi)的新劇《繁花》,說(shuō)雖然跟原著的差別有點(diǎn)大,卻依然在看劇時(shí)被戳中淚點(diǎn)。
作為外鄉(xiāng)人,大抵可以理解,在屏幕上看到自己身處的真實(shí)世界風(fēng)云翻卷時(shí),那種難掩內(nèi)心激蕩的心情。而要體察更幽深的情愫,須與這座城市骨血相融,絲絲縷縷都相親。
在上海十年,我的生活軌跡幾乎只圍著一截淮海中路打轉(zhuǎn)。無(wú)數(shù)個(gè)日夜,我?guī)缀踔蛔鋈拢合駲C(jī)器一樣工作,閑暇窩在咖啡館看書、畫畫,或者散漫長(zhǎng)的步。

淮海中路街景 IC photo 資料圖
淮海中路東起西藏南路,西至華山路,全長(zhǎng)有5.1公里。大多數(shù)時(shí)候,從比較靠近中段的位置出發(fā),或者從別處走到中段,三五公里恰到好處。十年似乎變化不大,但沿途每季總是各有風(fēng)情。
珠寶般璀璨的商場(chǎng)店鋪,和面目黢黑模糊的居民小區(qū)交錯(cuò)排布,時(shí)常能在建筑上看到標(biāo)著“優(yōu)秀歷史建筑”的銘牌。有的端莊厚樸,濃縮一段近代史;有的靜默無(wú)言,主人也漸漸不被互聯(lián)網(wǎng)世代們知曉。
樹影投在牙白墻面上,場(chǎng)景又令人忍不住想起王勃的“堰絕灘聲隱,風(fēng)交樹影深”。于我而言,淮海中路就是《繁花》里的黃河路。它確實(shí)也很像一條河流。
淮海中路潮人多,常有路人好看得像是徑直從50年前的巴黎秀場(chǎng)走出來(lái),帶著風(fēng)洄游。這里亦多豪車嘯叫飛馳,還有烏泱泱涌向武康大樓前拍照的人浪。搭公交經(jīng)過(guò)此地,經(jīng)常能聽見車?yán)餇斒鍤夂艉敉虏郏?ldquo;嘎洗多寧!啊伐曉得有啥好拍格!”
是啊,十年……哦不,一百年來(lái)武康大樓們都在那里巍然不動(dòng),人們走馬觀花隨浪去,無(wú)非掠得一張網(wǎng)紅同款照片。淮海中路,故事已經(jīng)塵埃落定,只余人與人互相游歷,有啥好拍。
幾年前,我曾在體育媒體工作,聽說(shuō)霞飛路(后被改名“淮海中路”)上曾出過(guò)中國(guó)第一代職業(yè)拳王,想要以此為題材做個(gè)內(nèi)容。拳王名叫余吉利,曾居住的霞飛坊(后改名“淮海坊”)就在我散步必經(jīng)地。
但這是一個(gè)消失的故事。1930年出生的拳王,十五六歲就常去當(dāng)時(shí)租界外國(guó)人舉辦的拳賽,贏回一把銀勺子或者一個(gè)皮帶頭。他逐漸成為西藏南路上大世界的拳擊明星,并在1951年成為上海市次中量級(jí)拳擊冠軍。
看到這個(gè)故事,我試圖聯(lián)系采訪過(guò)拳王的記者,和曾與拳王打過(guò)交道的上海精武體育會(huì),但他們告訴我,拳王已于2015年去世。這是我第一次確鑿地感受到淮海中路有人消失。
幾年之后,在淮海中路優(yōu)衣庫(kù)旗艦店對(duì)著的那個(gè)路口,每天上班都會(huì)遇到一個(gè)大姐。她上了點(diǎn)年紀(jì),但看得出年輕時(shí)十分好看。
如果非要形容的話,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(guò)《花與蛇:零》,浜田法子演的靜子,幾乎就是一模一樣的類型——不知道自己美麗,面容與眼神生出哀切,也不是故意的,好像天生就是如此,十分易碎的樣子。她幾乎每次都會(huì)攔住我,說(shuō):“美容……”而我不會(huì)等她說(shuō)完,就迅速閃過(guò)。
有一天,突然對(duì)那種易碎不忍,就停下來(lái)聽她說(shuō)。她十分討好地把我?guī)нM(jìn)旁邊的大廈,上樓,左拐右拐,一個(gè)簡(jiǎn)陋的門面,里面坐著兩個(gè)冷漠的年輕姑娘,她們讓我坐下來(lái),等人介紹美容項(xiàng)目。
我十分利索地逃跑了。那位大姐沒追上我。第二天上班,仍然看到她站在路口,但她沒有再攔住我。
很快,我因故離開了上海。一年之后再回來(lái),每次經(jīng)過(guò)那里,都會(huì)留意她還會(huì)不會(huì)在。然而沒有。就,又是一種確鑿的消失。